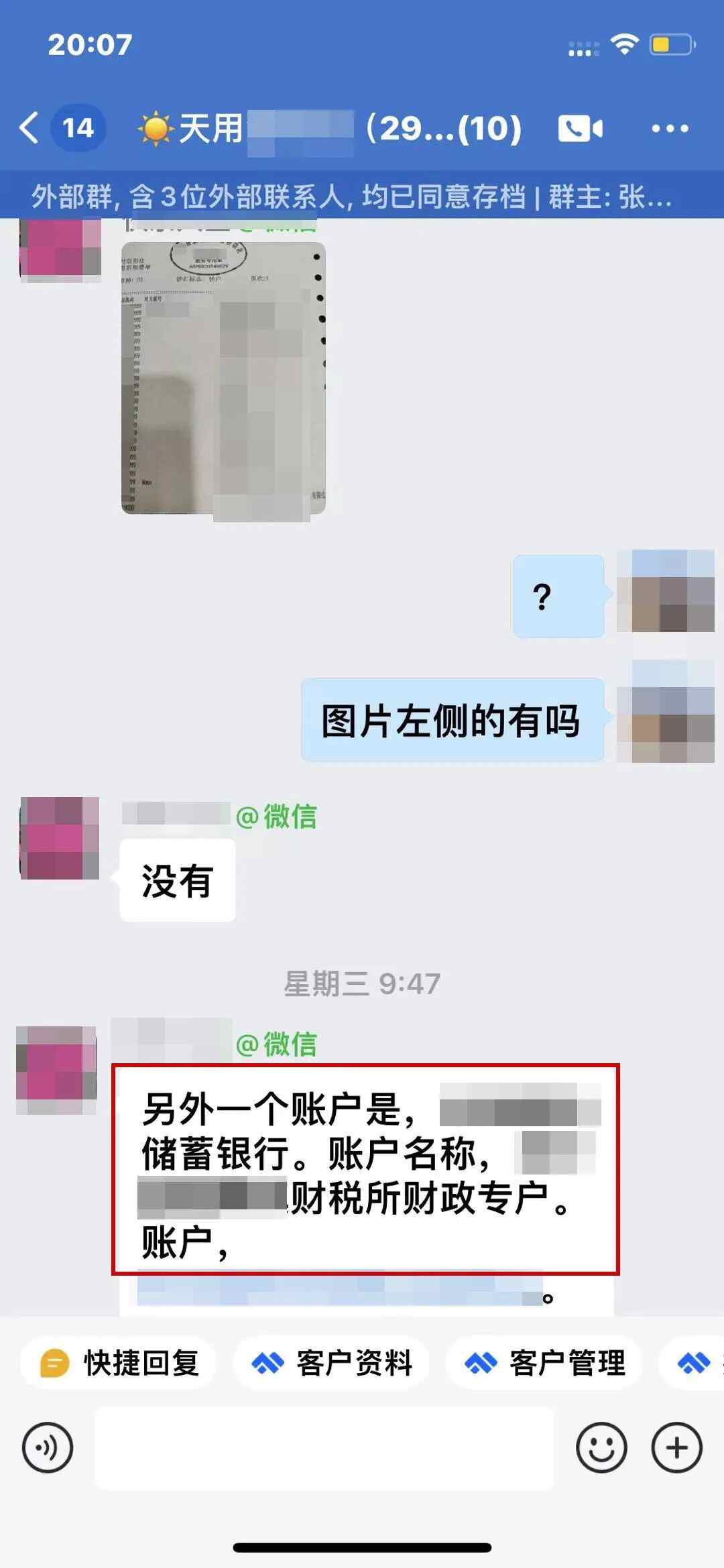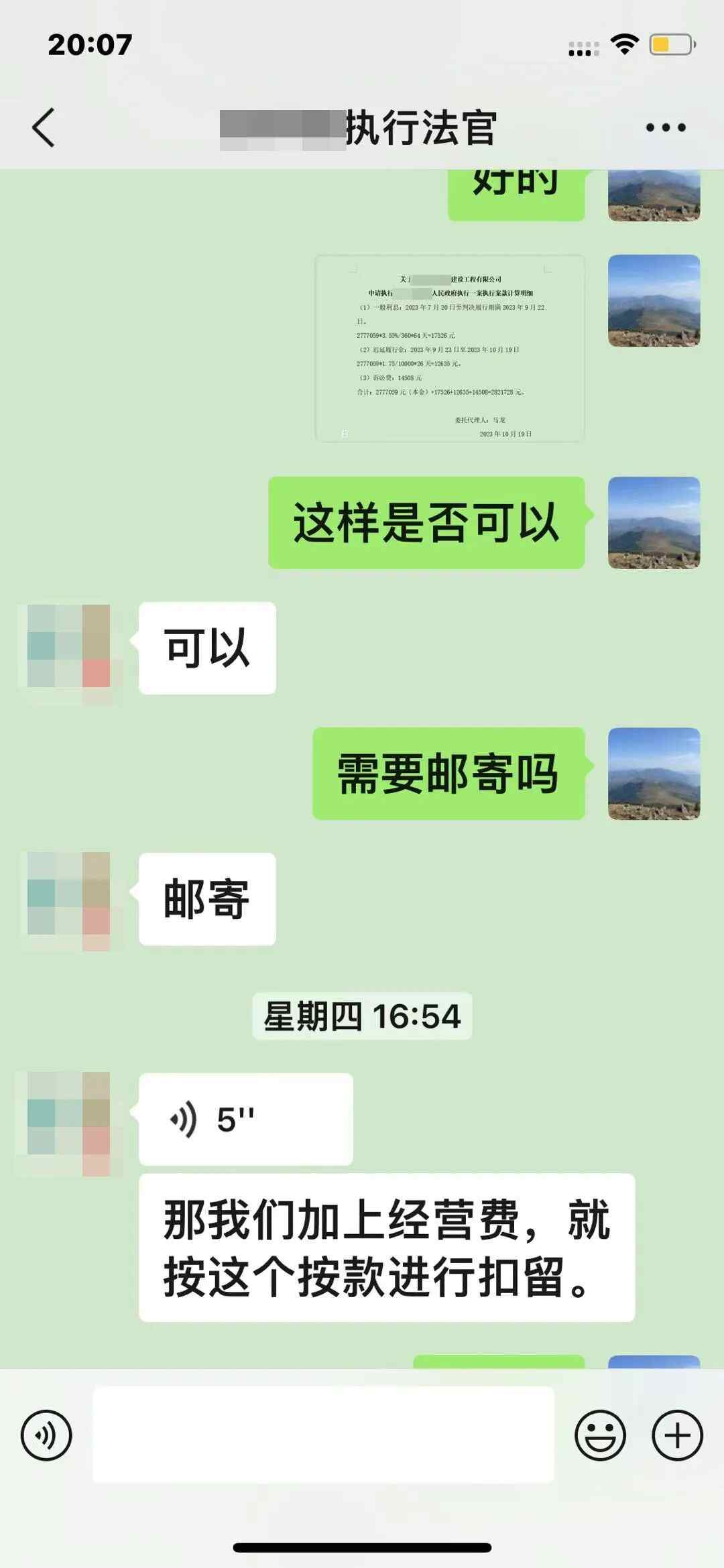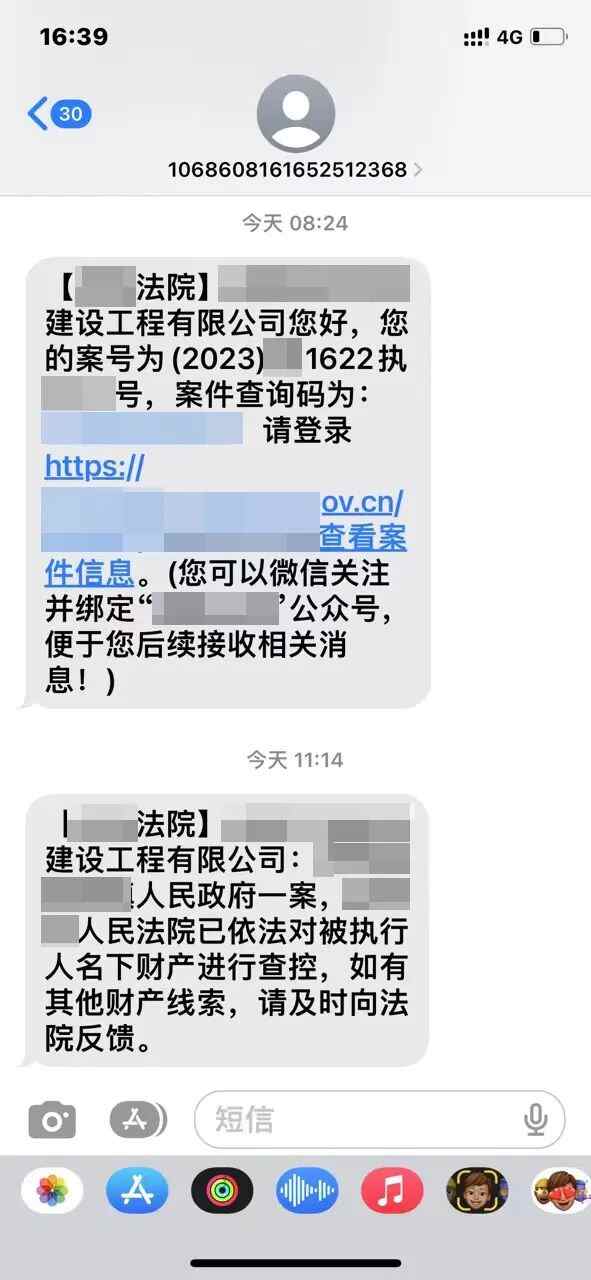想象竞合犯择一重罪论处
 崔玉君律师2022.01.17200人阅读
崔玉君律师2022.01.17200人阅读
导读:
而蔡墩铭教授则持否定的意见他指出既然想象竞合犯只选择一重罪科处不再论以轻罪而从刑是附加于主刑的刑罚轻罪既不科以主刑则从刑既无主刑存在而无所依附所以对于轻罪之从刑似不应予以宣告比较符合法理,而蔡墩铭教授则持否定的意见他指出既然想象竞合犯只选择一重罪科处不再论以轻罪而从刑是附加于主刑的刑罚轻罪既不科以主刑则从刑既无主刑存在而无所依附所以对于轻 ...,对想象竞合犯实行“从一重”处时只是要按照重的罪名定罪处罚并非对行为人所触犯的其他轻罪置之不理相反审判人员必须在判决书中载明行为人所触犯的轻罪名。
在这种情况下按其中的一个重罪定罪处罚。但是刑法分则的个别条文似乎规定了特殊的想象竞合犯以数罪论处。对想象竞合犯实行“从一重”处时只是要按照重的罪名定罪处罚并非对行为人所触犯的其他轻罪置之不理相反审判人员必须在判决书中载明行为人所触犯的轻罪名。而蔡墩铭教授则持否定的意见他指出既然想象竞合犯只选择一重罪科处不再论以轻罪而从刑是附加于主刑的刑罚轻罪既不科以主刑则从刑既无主刑存在而无所依附所以对于轻罪之从刑似不应予以宣告比较符合法理。关于想象竞合犯择一重罪论处的法律问题,大律网小编为大家整理了刑事辩护律师相关的法律知识,希望能帮助大家。
至于不以数罪论处的根据刑法理论上则存在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对想象竞合犯科处一个刑罚是刑罚适用上的合目的性的要求第二种观点认为对想象竞合犯科处一个刑罚是因为行为人只实施了一个行为作为评价对象的只有一个行为第三种观点认为之所以存在想象竞合犯的观念是因为对行为进行了重复评价实际上只存在一个违法第四种观点认为对想象竞合犯科处一个刑罚是因为行为人只是基于一个或者准一个意思活动而实施行为只是一次突破规范意识。我们认为上述几种观点并不一定冲突但客观上的一个行为与主观上的一个或准一个意思应是科处一个刑罚的最主要根据。
我国刑法分则的某些条文肯定了这一处理原则。例如刑法第329条第1款规定了抢夺、窃取国有档案罪第2款规定了擅自出卖、转让国有档案罪第3款接着规定“有前两款行为同时又构成本法规定的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如果窃取的档案是国家秘密则同时触犯了窃取国有档案罪与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刑法第282条如果擅自出卖、转让的档案是国家秘密则同时触犯了擅自出卖、转让国有档案罪与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刑法第398条或者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刑法第111条。在这种情况下按其中的一个重罪定罪处罚。
但是刑法分则的个别条文似乎规定了特殊的想象竞合犯以数罪论处。根据刑法第204条第2款的规定纳税人缴纳税款后采取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欺骗手段骗取所交纳税款的依照偷税罪定罪处罚骗取税款超过所交纳的税款部分依照骗取出口退税罪定罪量刑。如果行为人在缴纳10万元税款后一次假报出口骗取了20万元退税款的则分别认定为偷税10万元和骗取出口退税10万元并实行数罪并罚。这实际上是一个行为触犯了两个罪名但刑法规定实行并罚而不是以一罪论处。
具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更重要的还是得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从一重罪处罚需要依据以下几个具体问题进行判断
1、轻罪在“从一重”中的地位。对想象竞合犯实行“从一重”处时只是
要按照重的罪名定罪处罚并非对行为人所触犯的其他轻罪置之不理相反审判人员必须在判决书中载明行为人所触犯的轻罪名。另外若在裁判之前重罪遇有赦免还必须就其他余罪即轻罪处断。若最重之罪的裁判确定后重罪之刑未执行或尚为执行完毕之前处刑之重罪被赦免或因法律变更而不处罚时应免除刑罚的执行并不再就犯罪行为所触犯的其他轻罪定罪处刑。
2、附加刑在“从一重”中的适用。“从一重处”被认为是关于主刑的适用原则当一行为触犯的数个罪名中重罪没有附加刑或者重罪、轻罪都有附加刑时附加刑应当如何适用?在我国台湾地区学者们关注的较多并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意见。“肯定说”为孙德耕、梁恒昌等教授所主张。如孙德耕教授认为所谓从一重处断者以其性质本非一罪而法律规定从数罪中之一重罪处以最重之刑是以如有两个以上之没收时仍得予以并科即重罪无可没收之物而轻罪有可没收之物仍应以没收。而蔡墩铭教授则持否定的意见他指出既然想象竞合犯只选择一重罪科处不再论以轻罪而从刑是附加于主刑的刑罚轻罪既不科以主刑则从刑既无主刑存在而无所依附所以对于轻罪之从刑似不应予以宣告比较符合法理。
关于附加刑在“从一重”中的具体适用问题在我国刑法理论上探讨的并不够深入但也有不同意见。如有学者认为“如果对较重之罪仅科处某种主刑而较轻之罪根据情况即使存在着适用刑罚即须科处一定的附加刑的可能也不应于较重之罪的主刑并科。因为我们把想象竞合犯当作实质一罪处理的适用的处罚原则是从一重重处断对于较轻之罪已经没有适用刑罚的余地。”不过也有的学者持相反的意见指出“所触犯的轻罪中有应予没收的仍须按照刑法第64条的规定予以没收”。
一、行为人实施了一个危害行为。
这是关于想象竞合犯的认定区别于实质数罪及牵连犯等犯罪形态的根本点究竟何为“一行为”学界众说纷纭。有所谓“自然行为说”、“社会行为说”、“犯意行为说”、“法律行为说”等等。或以结果、或以性质、或以犯意、犯罪构成的个数来区分一罪与数罪虽各具价值但均有失偏颇只有“因果关系说”综合考虑行为、结果、行为与结果之因果关系这些客观要素来设定“一行为”的标准合“自然行为说”与“社会行为说”之长较为科学。根据“因果关系说”一行为包括“行为人的一个身体动作造成一个危害社会的结果的即一因一果是一个行为一个身体动作造成数个危害社会的结果的即一因多果是一个行为数个身体动作造成一个危害结果的即多因一果也是一个行为”而“数个不同性质的身体动作造成数个危害社会的结果的即多因多果是数个行为。”想象竞合犯中只要行为人实施了一个危害行为无论其行为是作为还是不作为其犯罪心理是故意还是过失亦或故意与过失混合均不影响想象竞合犯的成立。
二、行为人的行为同时触犯数个罪名所代表的数个性质不同的犯罪构成。这是想象竞合犯的认定区别于实质一罪的根本特征。
罪名是犯罪的名称是对犯罪构成的高度概括。关于想象竞合犯的认定何谓“数个罪名”如今尚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一行为触犯数个同种罪名当然是触犯数罪名是同种数罪。”中国台湾学者翁国梁也提出“学者有承认异种类之想象竞合犯而否认有同种类的想象竞合犯之存在者余则以为不然盖被害法益之个数并不限于同种或异种且刑法55条前段规定系置重于被害法益之个数。一行为而犯数罪名即具备数个犯罪构成要件并不因被害法益之是否同种而有异故也。”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实践中也是不必要的甚至是错误的。
首先如前所述想象竞合犯不是实质数罪原因在于行为人只实施了一个危害社会的行为。如果承认同种罪名是数罪名那么在想象竞合犯一行为的前提之下各犯罪构成的各个要件实际上均相互重合只是直接客体数量和范围的增加而这一量上的变化不足以影响罪质可为一罪构成完全概括只用一个罪名就可以完整评价故同种罪名仍为一罪。
其次即使承认同种罪名是数罪名对司法实践也并无裨益。如行为人故意一枪打死三人对三个故意杀人罪如何从一重?因而承认同种罪名的想象竞合犯不但对司法实践毫无意义反而徒增困扰。

再次承认同种罪名的想象竞合犯可能导致重罪轻判造成罪责刑无法达到一致如行为人故意用枪击伤三人致一人重伤两人轻伤如按想象竞合犯处理则从一重罪处罚只对重伤他人的结果进行评价而其他两轻伤结果则忽略不计这显然造成罪刑严重不一致枉纵了犯罪人对受害人也极不公平。而若按一罪处理则可综合评价将致三人受伤的事实作为情节考虑则可做到罪责刑平衡。
台湾学者从法益说出发进行了有益的探讨立论有据但由于中国大陆刑法理论的基础是社会危害性理论因而这一理论只能从一个侧面给我们一些启发却无法应用到中国的刑事司法实践当中来。
想象竞合犯不应包括同种罪名的情况只有当罪名相异犯罪构成性质不同时才存在着竞合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三、行为所触犯的数个罪名均无法全面评价该行为即行为所触犯的各犯罪构成之间应无重合之关系。
这是想象竞合犯区别于法条竞合犯的根本特征。
犯罪行为所符合的数个犯罪构成之间具有重合关系这是法条竞合犯的法律形式。重合关系包括包容关系和交叉关系那种不承认交叉关系或不完全承认交叉关系如马克昌教授在其想象竞合犯与法条竞合一文中指出“一法律条文之一部分为他一法律条文内容之一部分时不是法规竞合的提法似有不妥。所谓重合关系应为犯罪构成的各个要件均存在包容与交叉关系。
在犯罪客体上表现为既适用于范围较广的社会关系也适用于范围较小的社会关系在犯罪主体上表现为既适用于范围较广的主体也适用范围较小的主体主观方面的重合主要是罪过形式的重合主要是故意的重合既指内容较广的故意包括内容较单一的故意也指一般故意包括特定故意犯罪过失的重合则主要是行为人应当预见的结果范围之间的包容关系客观方面的重合表现在行为方式的完全相同行为的复合性包括行为的单一性或行为的多样性包括了行为的单纯性。
正是由于刑法法条错综复杂的规定才使得某些犯罪构成之间存在着相互的重合但另一方面也导致其中必有一个犯罪构成最符合该犯罪行为的本质特征能够完整评价该行为而排斥其他法条的适用因而法条竞合犯只是形式上触犯了数个罪名而其本质上是单纯的一罪。其构成由两个要件即其一犯罪构成的相互重合其二同时触犯数个具有重合关系的犯罪构成的行为的发生。
而想象竞合犯恰与之相反其行为所触犯的各构成并无重合关系使得其区别于一罪而具有不完整数罪的特征。想象竞合犯的出现是由于行为人的特殊行为而使两个本来并无重合关系的法条建立起了偶然的联系其出现于法典制定时是难以预见的。
 点赞
点赞
 收藏
收藏